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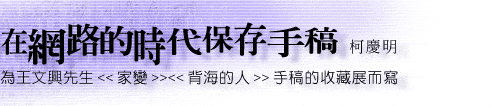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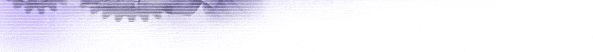
| 我喜歡寫字。或許是因為我所依賴的符號系統,是本身即可自成書法藝術的漢字。用手執筆(各式各樣的筆!);用筆在各類的紙上,行走或切割出一個個迷宮似的圖畫,就是我自童蒙入學以來最大的喜悅,更別說後來在文字的連綴之後所發現的,那無邊無盡的情意與思維的想像空間了!讀與寫;寫與讀,真的是我的通往上都之路! 但小時候自抄書作業開始,所養成的寫字習慣,卻被「電腦」這一具攔路虎所逐漸吞噬殆盡。輸入、鍵入漸漸就取代了我的「書寫」。雖然我的「寫字」總是只能得個「乙」;到了念大學,葉慶炳老師還對我說過:「你的這種粗粗大大的字體,考試時是會吃虧的!」但我還是頑固的喜歡自己那種平板笨拙的「寫字」。因為它就是我的那種「土樣子」!一種未經琢磨,也無矯飾的,平庸到見出不出個性美,卻也反映了我的不成形狀的平凡「個性」一一熟人一看就知道它們是我寫的「字體」,一種粗拙到別人不會也不能模仿的「字體」。但不論採用的是何種輸入法,電腦裡呈現或列印出來的卻永遠是各式各樣「標準」的字體。美觀上自然大有進步。但卻永遠讓我有一點心虛;甚至會有一種淡淡的哀愁,流漾其間,似乎有一部分的「我」,在輸入或鍵入之際流失了。 連接上網路之後,我的「寫作」,往往就要多一道,按一個「傳送到(D)」的手續,慢慢的這一按鍵,就成了我的「寫作」完稿的徵候了。只是當我發生歐陽修寫<相州晝錦堂記>一般,事後發現必須再加兩個「而」字之類的修改時,往往不能,也不需派遣快馬追回,大抵是以再一封電子郵件解決。在幾度訪談或記錄稿的校對訂正往返傳送之餘,我突然醒悟到:從此,所有的修改,都成了「船過水無痕」,我們再也看不到修改的痕了。並且幸虧在網路上往來逍遙談笑的都是德行高潔的鴻儒,否則幾個關鍵的字眼一改,再往通訊錄上的網址,按個全部傳送,豈不比在傳真機擺弄下的Paul de Man,更容易身敗名裂?於是,我發現Jacques Derrida 談了半天塗抹仍然留下的痕,終究只是「紙本」時代的思維,何嘗面對了網路時代的現實。 因而,我不禁深深懷念起紙筆書寫的時日,不僅是在紙上駛筆的奇妙感覺,師友們的龍飛鳳舞的筆下英姿媚態;甚至只以英文通信的友人,我總可以在信上感覺:大男人的Stephen Owen,似乎正拿著一截短短的鉛筆,像小學生一般很用心的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為我畫字而書的情景;熱心溫馨,對許多人像媽祖觀音一樣的Helen Vendler教授,她的字,卻揮筆似劍,披荊斬棘而來,倒也反映了她的博學與犀利。 但對我而言,最具教育意義的卻是:初任「現代文學」古典文學專欄編輯時校閱葉珊(現在大家都名從主人的改稱「楊牧」了)的一篇題為<詩經國風的草木和詩的表現技巧>的來稿,它是寫在美國校園習見,可以撕下的黃色筆記簿紙上,只是橫過來作直行書寫,它以隔行寫就,卻在空出的行裡,作了許多修改。因為在大二的暑假,曾經和幾位熱愛文學與寫作的同學,以<<葉珊散文集>>作範本,推敲過散文寫作的技巧。所以,讀來格外窩心!初看未改的部分,其實句句通順,意思也很好;再看修改之處,不禁擊節讚歎!精神與精彩,正是如王國維所云:得此一字,而境界出矣!自己深覺獲益匪淺,頗有悟入之處。多年後想起,不免後悔未曾將它扣留珍藏;否則,即使不論個人的因緣情誼,亦豈不是教育學生運思寫作的最好教材? 是的,只有寫在紙本上的原稿,才能在其書寫的筆上,見到作者的性情,甚至寫作之際的心情!以及作者運思修改之際的意匠心。 我在就學期間,稍稍涉獵板本校讎之學時,即已深深為歷代刊刻之際的訛變而興歎,因而早已體認,連他人在著作初期或刊刻之前的抄本都是彌足珍貴,何況是真跡原稿?但自己任編輯、作校對、投稿、出書---,一路走來,卻一方面,不免貴古賤今,竟渾然忘了古今同理,對於重要的原稿,不論是他人的或自己的,原應知所愛惜;一方面卻也發現,科技的進步,除了照相製板之外,對於「真本」的流傳,幾乎少有改善。因為校對之事原本不易,學問的積累日益廣大,作者的表現方式風格考量亦愈趨自由多變,校對者未必能事事前知,往往愈校愈亂。往往發現親自校出的錯誤未改,而其他的校者依其自我認知的「改錯」,甚至電腦一個按鍵的不小心,都會在出版的紙本上,長久「銘印不誤」了。 尤其在以已發表的印刷文字,結集出書之際,幾度望著顯然被排印錯誤的段落,苦苦思量,卻追憶不起昔日的靈感時,就不禁要喟歎:「原稿!原稿!只要原稿還在就好了!」 但是,不管是否作好心理準備,我們卻已經悄悄的進入沒有「原稿」,甚至沒有「原本」的網路時代了!因而,對於現有,以至倖存的「手稿」,是不是該更積極更用心來保存? 幾年前陪同費海瑾師母等人前往中央圖書館特藏室察看收藏手稿的情況,發現其設備與管理足以妥善保存。一方面贊同師母將屈翼鵬老師的手稿捐贈給中央圖書館收藏;一方面不免遺憾,台大總圖缺乏相等的設備與管理。因而不敢為台大,向師母作任何的建議。但屈老師畢竟在中央圖書館任過館長,總覺得也算稿歸其所。 至於大半生任教台大,在台大宿舍終其天年的臺靜農老師,總覺得他的手稿,應由台大來特藏保存。因而,在得知霧峰林家頂厝,於九二一震災餘,將櫟社、萊園詩會、林家等相關手稿文物,捐贈給台大新總圖保存,觀覽了「特展」,深為感動之餘,就邀約了我們中文系的葉國良主任,在吳明德館長的引導下,參觀了台大新總館的恆溫、恆溼、二氧化碳防火,並有保全的特藏設備;以及在尊重捐贈者的意願下,另作副本、微卷(將來應作光碟)供人閱覽等管理措施後,並且在一一徵詢了多位參與遺稿整理的師長,皆獲同意,決定等當時主其事的林文月先生返台之際,即將目前暫鎖在中文系保險箱的臺老師遺稿送交總圖特藏。 正在此段期間,我因被選作圖書委員,就建議吳館長:台大總圖應有計劃的特藏近、當代文史哲名家的手稿,尤其是重要的文學創作的原稿。結果獲得熱烈的回應,總圖還擬訂了一個收藏的計劃。初步的主動邀約請求,為了比較容易獲得捐贈者首肯,決定由我先向相關的校友等人進行接洽,將來再擴及其他。正好王文興老師的<<背海的人>>下冊出版不久;他又送了我一部上下冊全套,我看到他在<序>中說:他花了廿三年餘寫這本書,卻又花了一年抄稿,又再花了一年在出版校對上。我就想王老師這種一髮不苟,字字皆有無窮意蘊與匠心的著作,「原稿」一定要保留!精神的貫注姑不論,光是後來的出版與研究,若無原稿,恐怕處處難以定奪。 本來以為得等到開學之後,才能向他請求。竟然暑假期間就在捷運公館站偶遇。沒想到我一開口,王老師就很爽快的答應了,並且說起李家同先生任靜宜校長時,也作了相同的請求,他考慮了很久,結果他沒有答應。在我連絡吳館長帶王老師參觀了總圖的特藏設備後,王老師很快的就將<<家變>>與<<背海的人>>以及一些相關資料手稿捐贈總圖。 台大總圖亦以此勝事為本學期活動的重點,不但將於校慶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時,請陳維昭校長主持此次手稿捐贈特展的開展儀式;並且將假總圖國際會議廳舉行:1.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十時起,由中文系梅家玲教授主持「與王文興教授談文學與寫作」的座談會,特別邀請清華大學外語系的廖炳惠教授與中央大學中文系康來新主任來和王文興先生對談。另外,在相同場地,時間則改為下午二點半起,安排了三場專題演講,各為:2.十一月三十日,請柯慶明教授講王文興先生的<<十五篇小說>>;3.十二月七日,請梅家玲教授講<<家變>>;4.十二月十四日,請鄭恆雄教授講<<背海的人>>。王文興先生聽了總圖這個計劃本來一再謙辭;經我們一再保證,後續還有臺老師等人手稿的捐贈與相關的活動,我們這一類的活動會一路持續下去---,我們正好藉此向社會宣告我們的計劃與我們收藏當代文學手稿的用心。王老師終於被我們說服,而應允了那場談文學與寫作的座談。 後來,我在中正大學「台灣文學史料編纂」研討會上,遇到國立臺灣文學館的黃武忠先生,談起台大總圖開始收藏近、當代手稿的計劃,他也同意我的能夠妥善保存重要手稿的地方越多越好的想法。位於地震帶的台灣,實在沒有把雞蛋只放在一個籃子裡的道理。黃先生補充說:「只要能以副本互相支援;以網站互相連線,方便各地的研究就可以。」那麼,讓我們在網路的時代;大家一起來保存彌足珍貴的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