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先生上次返台請吃飯的時候,齊邦媛老師突然問我:
「慶明,你叫林先生:『老師!』,你上過她的什麼課呢?」
面對滿座的真正上過課,或由她指導過論文的「正牌」學生,我只有老實的回答:
「我沒有正式上過林老師的課,但林老師是我童年時的文學啟蒙『老師』,我後來決心第一志願讀中文系,也多少受到她的影響!」
我是被父母戲稱為:「吾家的文學少年」而度過幸福童年的,當時最得意的事情,是遍買又遍讀了東方出版社與啟明書局的所有的兒童與青少年文學作品。日漸成長而開始往所謂世界名著泛濫之後,就漸漸的忘記了自己在當時閱讀的是哪些書籍。但在那廢寢忘食、神魂顛倒的歲月裡,很怪異的竟然只有一位編寫者的名字:「林文月」,深印於我童稚的心靈。林先生一定沒有想到她在二十幾歲時改寫的文學名著與偉人傳記,竟然啟發了我一生的文學興趣與鑑賞品味‥‥‥
就在整理林文月先生的捐贈以作展出的準備之際,我發現了我所以會只記得林先生名字的緣由:她所改寫的文學作品,原來竟是我青少年代最喜愛的《基督山恩仇記》與《小婦人》;《茶花女》雖然不是我的最愛,但那淒美哀感的境遇與愛情,確亦強烈的震撼了我的天真心性。而三本傳記:《聖女貞德》、《南丁格爾》、《居禮夫人》,她們三人,對我而言,更都是神聖的存在。父親的醫學背景與對科學研究的興趣,使他一直崇拜居禮夫人與南丁格爾,無疑亦影響了我對她們的感覺。但對宗教與神祕精神經驗的好奇,卻更使我對聖女貞德著迷。這些作品與人物,後來我自然都反覆的讀了中譯或英譯的更完整的版本,甚至都看過改編和拍攝的電影;但基本的印象,卻是早已奠定,規範了我的價值取向和處世態度!我不禁要反過來想:會去編譯、改寫這些作品與傳記的林先生,在她的選擇中,又反映了何種性情?何種胸襟?(這是以前所沒有想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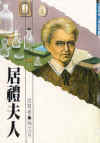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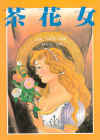
我還記得那本書的素樸的封面:白底上除了黑字的書名,編、著者之外,就是一小塊黑痕般的漢代畫像磚的圖案。林文月先生是我當時的典範人物,但除了白紙黑字,我對她沒有印象。當時的書後並不附著者的相片,那是文星叢刊之後才有的習慣。面對著提 供展出的,林文月先生大約是她在編寫撰著我所耽讀的那些故事與論文年代的,一張她站在台大講台上講課的照片;我在當時真的「不知道」她是這樣的「先生」!是聖女貞德的神祕熱情+居禮夫人的聰慧專注+南丁格爾的溫柔慈悲‥‥‥?我不禁想起,那已是我自己已然教書多年之後的一班中文系的畢業專刊上,同學們寫著他們對上課中老師們的印象。有人寫著:「坐在教室裡,看著講課中的林文月老師,覺得真是風華絕代!」自然我聽過林先生的學術演講,但卻是錯過了聽她講課的機會!她的授課風貌是我所不知道的,只有這張照片可以想像了‥‥‥

真正「見到」林文月先生,是就讀了台大中文系,進第四研究室找葉慶炳老師之際。不算寬敞的第四室,不但放置了「四部備要」的集部,而且是五位先生共用,當中靠著中庭窗戶的一張書桌,其實是鄭騫(因百)和葉嘉瑩(迦陵)兩位老師對向合用,當時鄭老師在國外,所以葉慶炳老師也用那張桌,由於門口有書櫃屏風遮蔽,右手邊的另一張較小也較隱蔽的書桌坐的是王保珍先生;林文月先生的座位,是左手邊靠牆的另一張小書桌,事實上是當著門口通路,林文月先生一直在那張小書桌,背門而坐,直到榮休為止。
這個研究室最熱鬧的時候是七位教授合用。在那裏還能夠讀書寫作,還真需要定靜功夫。那天我一進門,正好葉老師在,林先生正埋首寫作,被我驚擾而抬頭來,葉老師就對我說:「柯慶明啊,這是我們系的才女,林文月先生!」我一方面驚異她的年輕;一方面脫口而出:「啊!我讀過您的好多文章!」然後囁嚅不知以繼‥‥‥
由於幾門我最有心得課程的任課老師:大一葉慶炳老師的中文系「國文」,大二、大四葉嘉瑩老師的「詩選」、「杜甫詩」,大三、大四鄭騫老師的「蘇辛詞」、「元明戲劇」,都用第四室,而我一直有課後纏住老師繼續討論的習慣,所以我就成了進出第四室的常客。少不更事的我,一直沒有注意到這既妨礙了任課老師需要的休息;其實也干擾了其他先生的工作。每每在我固執己見,轉不過彎來時,(大概是已被干擾了的)在旁聽到談話的林先生,會突然用一兩句精要的話語,猶如撥雲見日的插入指點,於是我豁然而解,心悅誠服‥‥‥
這些經驗加上早年的閱讀,始終使我認為林文月先生之所以為「才女」,就是其天生穎悟,聰慧特出的自然表現而已。但是在展出前檢視著她所珍藏,大三上鄭因百老師的「詞曲選」「陶謝詩」的課後整理心得的筆記。看著那用工整娟秀的筆,寫得滿滿三大本,不但記老師上課的要點,更將自己聽講的引申,閱讀的體會,一一記下,寫成完整的論述;突然覺得它們的珍貴不僅是鄭老師的紅筆批點,師弟兩人彼此激盪,相引相生的慧見巧思;而更在林先生的好學深思、專注用心。難怪一起檢視的淑香要讚歎:「這真的是台大學生的模範!」
正如我有許多年,天經地義般的視臺靜農老師就是「智慧長者」;壓根兒也沒想過他也當有過徬徨少年時;即使畢業後留系當第三室助教起,不知不覺已是三十餘年,我想到的林文月先生一直是「老師」。看了她的筆記,知道了她作學生時的用功。看到了她這時期的照片,才發現她也有天真可愛,甚至頑皮的一面。尤其一張大一的半身照,被特藏組的夏麗月主任宣稱為「像電影明星一樣」的,流漾出一種如夢似幻的氣質,用敻虹的詩句:「在最美的夢中;最夢的美中」,恰是最好的形容。我才突然醒悟聖女貞德,也可以是美麗的,於是想起少女時期的殷格麗‧褒曼所扮演的貞德,其實真是秀外慧中!林文月先生的碩士照亦給人類似的感覺‥‥‥

我自己是台大中文系最後選修學士畢業論文的人之一;因此我對林文月先生的學士論文手稿特別有興趣。(她的碩士論文,則已被印成「台大文史叢刊」之一了!)但是有趣的是這份存稿是三手抄成的;有林先生的筆跡,亦有當時還是男友的郭豫倫先生的筆跡,還有妹妹林文仁的筆跡。真的是一份充滿了愛情與親情的手稿!
在畢業論文還是必修的時代,原本一定是交給成績股查存,若干年後銷毀。以鄭因百老師謹守規矩的個性,一定照辦如儀;但又愛惜學生的心血,才又由他們自行抄存。我那時因為已是只算兩學分的選修,加上早已超修了二十幾個學分,所以在原訂的七部分只完成了四部分,卻已連附錄近四十萬字,來不及完成下,就義無反顧的先去金門當兵了。因此,通達的臺老師就只給了成績,卻將原稿留到我返系任助教後,才交給我繼續修改,所以我反而不知道得自行抄存的故事。
八九萬字的論文,在只能一一手抄的年代,其實是苦工。淑香看了說:「這就像托爾斯泰夫人反覆為托爾斯泰抄謄《戰爭與和平》的手稿一般」;我說:「郭師丈贏得林老師佳人芳心,良有以也!我們的弟弟妹妹,大概也不會為我們這樣的抄稿子吧!」其間所蘊蓄的情意,自然也是我們所不知道的。



